| smen | 2020-07-15 12:33 |
|
公园厕所。 一位阿叔走到小便池。 他的眼神不自然地往旁边瞟,身体靠近。  对方察觉到了异样,很快,拉上裤链离开厕所。 看来,他找错了人。 离开公厕后,阿叔继续在公园闲逛,这时一位石椅上听歌的人闯进他的视野。 两人四目交投,相视一笑。  好像有一种默契。 “你好.......你经常来这里吗......我叫阿海。” “你要不要进去?” “不如,做下朋友先。” “下次先吧。” 起身,阿叔离开了公园。  感觉这聊天……有一搭没一搭? 其实每一句,都是试探性的谜面。 谜底,在这里揭晓—— 《叔·叔》  《叔·叔》大胆。 在华语电影中,同性恋题材仍屈指可数,《叔·叔》的镜头,推向了一个更边缘的群体—— 已婚的老年同性恋。 这个标签上,每一个词,都是可以引爆争议的雷点。 《叔·叔》也小心。 在大胆的议题下,毫无说教。 甚至可以说,两个老男人,演出了今年最细腻动人的爱情片。 这份爱,有着难以想象的维度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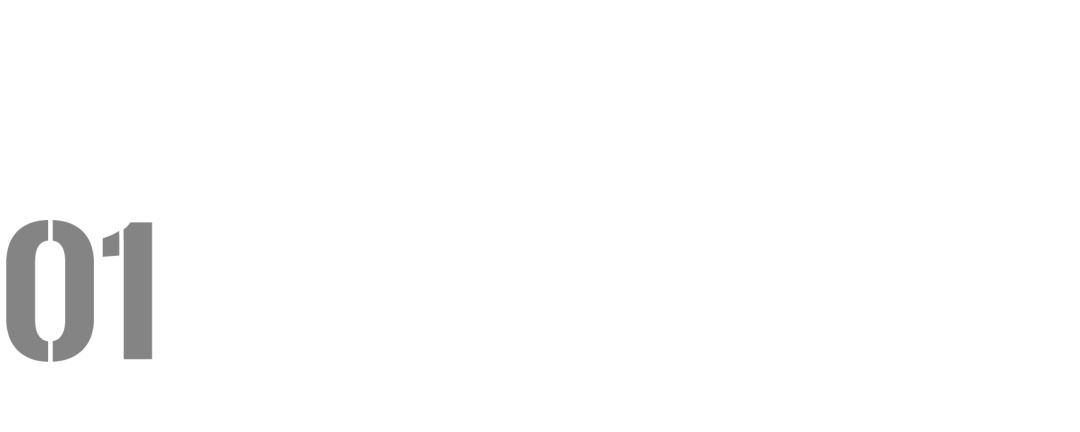 上半生 阿柏。 70岁了,但他依然不认老,开着的士“搵返两餐”。 他有个传统意义上的“幸福家庭”,有车有楼,儿女也成家立室,有空还会接孙女放学。  平时他会去一个公园“觅食”。 就像开头那样。 阿海。 比阿柏轻松潇洒。 他也结过婚,但后来离了,一个人带大儿子。 虽然说他有更多时间,去同志骨场混圈子,但要坦荡出柜,也难。 他很早离了婚,和儿孙住一起。 儿子是虔诚的基督教徒,怎么和他承认宗教里禁忌的同性恋呢? 父子之间从未碰过这个话题。 但儿子好像隐隐已经猜到—— 时不时提醒,“不要再孙女面前说这些”。 一次,不知情的妻子问阿海去参加什么人的喜酒时,他翻了脸: 你不觉得你今晚很吵吗?  这也是儿子给出的底线—— 我可以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但你也别想要出柜。 如果说年轻的同志出柜,要面对的问题是今后如何面对别人的目光。 而老年同志,则是要打碎过往的生活。 谁都想做自己。 但前半生,已经是沉没成本。 现如今最好的选择,只能是苟且了。 家里照顾好,自己生理和情感的需求,就偶尔出来透透风。 阿柏时常说自己要去深圳几天。 但出门,连“回乡证”都忘了拿。  两个叔叔,就是这样躲躲藏藏、遮遮掩掩,牵上的手。 他们都太懂得分寸。 一开始,阿柏提出载阿海回家,阿海笑道:“你一定要打表哟!” 阿柏笑着说:“我不收朋友钱的。” 但下一秒,阿柏让阿海坐回后面,不是副驾驶座,两人还没有敞开心扉。  一来二去,阿海才坐到了阿柏的旁边。 证据就是,阿海终于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,而且手还自动自觉地扣在一起。   起初两个人分别后,阿海发来“老奶狗”表情包。  但阿柏第一时间不是感觉甜,而是走出家责怪他—— 不要这么晚了找他,大家是有家室的人。  点点滴滴的积累,稀松平常的生活,都是两人在彼此的心中划痕。 第一次来到桑拿,阿柏还是好奇和拘谨。  但阿海已经轻车熟路。  这一场床戏,让人大呼意外。 拍两个大腹便便的老男人,满身赘肉,又不是梁朝伟和张国荣,审美上到底难以接受。 但错。 毫无猎奇或是辣眼。 一切的发生,都让人觉得自然而然。 叔·叔。 终于把中间的点拿掉,零距离地接触,融入了对方生命。 所有的镜头和特写,都很常规。 但你第一次看到,那布满皱纹的身体和身体,手和手,脚和脚亲密地依偎在一起。 那其中,有一种惊人的美和生命。    《叔·叔》能拍成,找演员就花了不少时间,导演整整试镜了100多位演员。 幸运的是,他们找对了人。 饰演阿海的袁富华,曾经因为《翠丝》中出演跨性别者获得过金马奖最佳男配角。  而饰演阿柏的太保,则拿下今年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。  他们细腻动人的演出,让整个故事看起来毫不别扭。 就像电影中旁人说的—— 我打赌你们两个在一起了10年,对吧?  两人的相遇,改变了两人的晚年生活。 他们似乎将对方纳入自己的晚年人生。 似乎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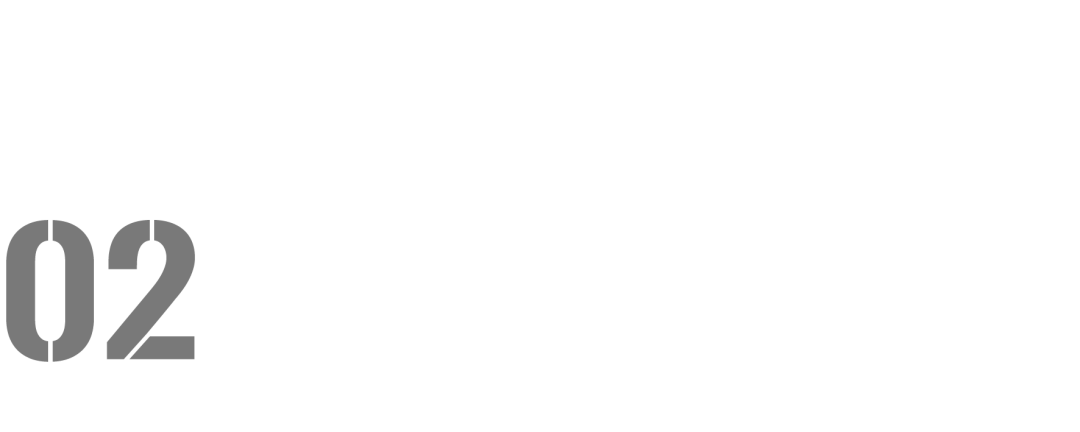 下半生 阿海就好像阿柏的引路人。 他带阿柏认识了解香港的同志圈子,同时也是导演杨曜恺想讲给观众知道的事情。 如果说同性恋处在我们社会的边缘,那老同性恋则是边缘的边缘。 《叔·叔》的剧本,是导演参考了学者江绍祺《男男正传》写成。这本书记录了香港“老同志”的日常生活,是香港LGBT运动重要的著作。 导演杨曜恺说,拍摄《叔‧叔》源于一个信念:“希望让这班年长同志知道,他们并非唯一有过这种经历的人。” 而电影中的柏,现实中其实有原型,可惜导演想再找他时,他已经不在人世。  △ 图片源自《明报》 在《叔·叔》里面,我们可以见到同性恋暗自生长出来的秩序。 他们有同性恋专属的公园、桑拿、夜总会...... 大家互相依偎,互相取暖。 但这些场所都有个共通点:暗。 象征着他们终究见不得光的尴尬。 缺乏权利的他们,公共空间一直被挤压,只能躲在一起,自成小楼,隐蔽和安全。  但是,他们终究是有权利去争取公共空间的。 这种公共空间不单单是物理意义上的。 还是社会地位意义上的公共空间。 香港同志文化以年轻主导,协助年长同志的机构寥寥无几,如何保障年长同志的生活,一直没有足够的关注。 电影中提出了“同性恋养老院”的构想。 为什么要特别搞个“同性恋养老院”,普通的不行吗? 其实同性恋的私人空间未必和异性恋一样。 他们可能会在房里贴些同性恋的海报,有一些自己的影碟或杂志,自己“特别”的衣服,甚至是挂彩虹旗。  这些东西也许不方便向外人展示。 而且“养老院”象征着人生的终点。 如果能和同性恋朋友度过晚年,大家同声同气,住起来也会比较开心。 最后,如果能以同性恋的身份死去,对他们来说,是操劳半世最大的安慰。 但是要建成同性恋养老院。 需要有人愿意到立法会抛头露面,这等于公开出柜。 这一点直接吓退了他们,大家都心有余悸。 比如超仔。 他曾经被电视拍过他出现在撑同志运动,但被邻居认出后,直接对他投以怪人式的眼光。  △ 对白:我以后都不会在公共场合说话了 但大家最怕的都是被家人知道。 “老同志”之所以一直被忽视,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碍于家庭,不敢发声。 这是本片贯穿始终的矛盾,一方面要维护传统的家庭,但另一面要真实地面对自己。 阿柏和阿海同样有这个顾虑,两人都不希望被家人知道。 这样是老年同志的尴尬。 同性恋的“恋”或身份认同,这或许是年轻人更关注的问题。 而在他们的年纪,有限的生命,生老病死的沉重,已经限制了他们去追求更多属于自己的人生。 孔子说“七十从心所欲”。 好像一个人到了老年,不用工作了,子女成家了,可以自由了。 但从心所欲后面还有下半部分—— “不逾矩”。 谁能打破?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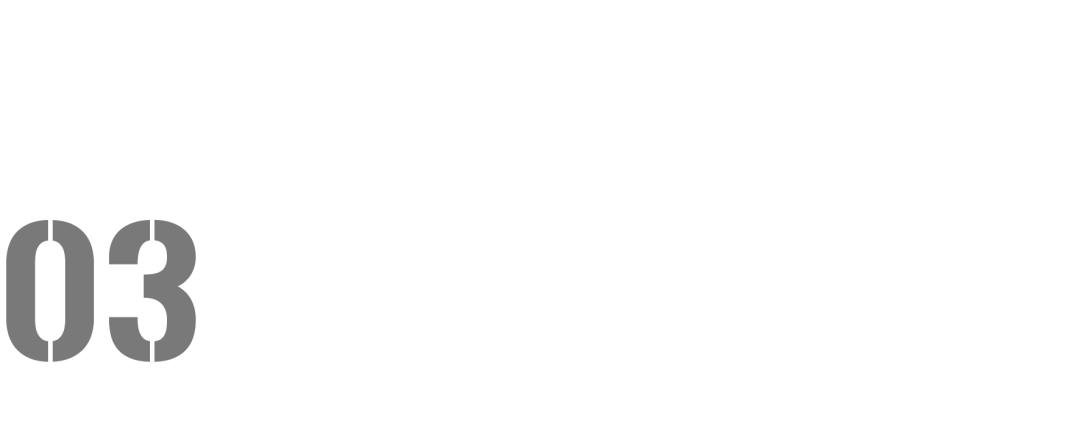 望来生 阿柏和阿海最顾忌的,倒还不是社会的眼光。 说白了,是中国人最看重的家庭。 而展现家庭的部分,是通过吃饭。 吃饭的座位、速度、夹菜给谁、聊天的话题,这些礼都是中国人的人情密码。 比如这场吃饭戏。  阿柏老婆夹鸡腿给大儿子,却没有夹给女儿。 很明显,他是不满意女儿带回来的男友。 电影里没有明说,但听女儿男友的口音,他是来自大陆的新移民。 一贫如洗的他,受尽丈母娘的冷眼,于是也把气发泄到女儿身上。 男友当然读懂了空气里的尴尬,见到丈母娘不给自己女友夹菜,他便自己夹鸡腿给她。 这一切,阿柏都看在眼里:这男人是爱自己的女儿。  这一场戏,导演是细腻的,并没有来个定格来个特写,只是一扫而过,提醒观众留意他们的表情。 点到即止,没必要“画公仔画出肠”。 女儿喜宴办酒,阿海以阿柏同事的身份出现,但见到阿柏的表情,妻子马上明白,就是这个人。  《叔·叔》的故事,不可避免会遇到通婚的问题。 现在豆瓣上顶的最高的评论也是—— “把别人牵连进来,就是不可原谅。”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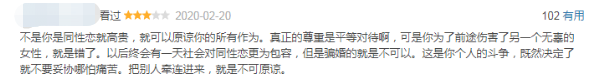 我们今天看一部电影,最习惯的就是用“三观”来过一遍安检。 是的。 你挥舞着你的正确。 因为它拿在你的手上,轻飘飘。 不可否认,伤害确实存在,电影也并未回避—— 比如,妻子做了大闸蟹,阿柏说不想吃,她就收了起来。  在深夜里,阿柏和妻子会长久地独处。 好像这样彼此才比较好过。  虽然两人从未道破,阿柏对妻子,对家庭,也很尽职尽责。 但他给妻子的爱,始终是缺位的。 可这是他的选择吗? 你当然可以说,同志就不应该选择进入婚姻。 但别忘了,这是今天的“正确”,当年的“正确”可不是这样说的。 在年轻的时候,叔叔的身份是过错。 没有人告诉你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,所有人必须生儿育女,家庭美满。 如果你不想,那说明你有病,你得改。 到了老的时候,他们循规蹈矩的选择,还是过错。 彩虹没有为老年同性恋带来平权。 只给他们抹上了新的污点。 此时错。 彼时也错。 唯一能够期盼的,只有来生。  阿海送了阿柏一个十字架,说道:“我的儿子劝我信教,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,你可以知道去哪里找我。” 这是阿海“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”式的隐晦告白——下辈子,我们在一起。 可是这种山盟海誓,对阿海来说太沉重了,他无法舍弃自己的家庭。 他说了句:“我家没有人信教的。” 阿海心里明白,阿柏选择了家庭。   这部同志版的《廊桥遗梦》,没有刻意渲染苦痛,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,一切都那么淡,就如主题曲《微风细雨》的歌名那样。 做道德判断是容易的。 但人生从来不是黑白分明。 《叔·叔》正是试图用他们的视角来呈现给我们看,事情其实还有另一面。 发掘人性的幽暗、善良和矛盾,呈现人性的多面复杂,让观众看完后做道德表率时,能多几分迟疑和保留。 正视自己作为人的七情六欲。 这才是“超越”的第一步。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