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的脚步停在第一级石阶上。风便来了。不是人世间那种断断续续的气流,而是完整的、浑厚的、带着旋律的实体。它从群山的褶皱里诞生,穿过万年蕨草的叶隙,掠过玄武岩的锋棱,生成自己的语言——“呼啦”,是掠过千年樟树冠的畅快,“噗嗤”,是穿过石窦孔穴的俏皮。

这风不是路过,而是专程为登山者奏响的序曲。它缠绕在膝间,推送在背后,分明是一只只清凉透明的手,扶着你的臂膀,将你从沉重的尘世里轻轻拎起,送入另一个维度。
石阶是骆越古道的遗存,被无数朝圣者的步履磨出了玉的光泽。阳光垂直地灌注下来,不像平原上那样斜着扫射,而是整桶整桶地、毫无保留地倾泻。
光与风在这里达成了某种契约:光负责澄澈,将远山近树洗刷得纤毫毕现;风负责流动,让万物在绝对的清晰里不失柔和。
走着走着,云雾便从山壑里漫溢上来,先是缠绕脚踝,继而漫过腰身,最后在头顶聚成拱穹。这时你才惊觉,自己已不在行走,而是在云中泅渡。群峰成了浮岛,在乳白色的海洋里时隐时现。

然后,你看见了那位“寿星”。在正前方的云幕上,一个庞大而安详的轮廓渐渐显现。饱满的天庭,长垂的耳廓,微微挑起的嘴角——不是刻板的画像,而是活生生的、有呼吸的形态。
云在流动,他的表情便在流转:时而慈祥垂目,时而眉梢轻扬。风忽然改了韵律,从先前的奏鸣曲转成了低沉的吟诵。那是在代他问候每一个远来的灵魂。
这便是“接寿”的由来了。山下村落里的百岁老人说,这不是迷信,是一种交换:你以虔诚的脚步丈量这座圣山,山便以风的韵律回应你。你的诚心,被云幕后的神明看见,他就会在你的命理数线上,轻轻打一个结,一个延长的结。
这观念如此根深蒂固,以至于山下那些吃着粗茶淡饭、穿着补丁衣服的老人,都将活过百岁视为理所当然。他们并非不老,只是那老去的形态里,有一种与天地同步的从容:皱纹里刻着山风的纹路,眼眸里映着云海的变幻。

我们继续向上,风势渐强,将云雾撕开一道缝隙。视野豁然开朗的刹那,一片嶙峋怪石扑面而来。它们不是温驯的摆设,而是有锋芒、有脾性的存在。一块巨岩如怒目金刚,另一簇石笋如列队军士——这分明是古骆越王麾下大将的魂魄所化,依然保持着拱卫王者的彪悍姿态。
我伸出手,指尖触碰冰凉的岩壁,仿佛触碰到一段被石化的时间。
就在这时,风突然静止了。
不是寻常的停歇,而是万籁俱寂,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像被吸走了。紧接着,前方一块状如王座的巨岩上,空气开始波纹般荡漾。一个身影由淡转浓,头戴羽冠,身披某种兽皮与丝帛混合的袍服,眉眼深邃,正是壁画上骆越王的形貌。他没有开口,但声音直接在我心中响起,是风穿过石缝的共鸣声:
“你为接寿而来?”我怔在原地,意念慌忙回应:“是……也为寻访王的踪迹。”

他微微一笑,周遭的岩石仿佛都柔和了轮廓。“世人总以为长寿是向天索取,却不知它本就在这山风里、云雾间,自由取用。你看——”他袍袖微拂,静止的风忽然重新流动,这一次,我“看见”了风:它们不再是无形的气流,而是一条条银亮的、半透明的丝线,从无穷远的天空垂挂下来,缠绕在每一棵古树、每一块山石,以及我的手腕、脚踝,甚至心口之上。
“这是‘风纹’,万物的寿数在其中流淌。”骆越王的声音如同远古的雷声,低沉而威严,“急躁的心,抓不住它;贪婪的心,会扯断它。唯有像这山一样坦然,像云一样自由,它才会轻轻系住你,经年累月,延展你的光阴。”
我凝视着手腕上那根几乎不存在的银线,它随着我的脉搏微微颤动,另一端消失在无尽的虚空里,云海连天的飘渺中。“那么,‘接寿’接上的,究竟是什么?”

“是节奏。“骆越王说。他的身影开始变淡,如同墨迹溶于无尽的洁白云海,“是让你的呼吸,合上这座山的呼吸;让你的心跳,应和这片山峰的心跳。山下那么多一活就轻松越过百岁的人,他们不是‘不死’,只是早早深谐了这歌谣的含义,所以有事没事就到这山上来,接些寿缘回家……”
话音未落,骆越王的身影已彻底消散在云海。风恢复了寻常的姿态,哗啦啦地吹,仿佛刚才一切只是幻觉。但手腕上那若有若无的触感,却真实地还在。
终于,我们登上山顶,海拔2888米至高。
这里是风的源头,云的故乡。蓝天伸手可触,白云则在脚下汹涌,成为一片无垠的纯白大地。远方的城镇、尘世的烦嚣,俱已沉没。世界在下方,而我在中央。

所有的山风,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,它们不再杂乱无章,而是汇成一首雄浑而恒久的合唱。这歌声没有歌词,只有无尽的韵律,它在言说:此间一刻,尘世一年。它是在为所有登顶者,加冕一曲长寿的歌。
顶坪一侧,竟真有一座小小的石砌祭坛,形制古拙,不知何年所建。几位早到的登山者,正安静地排着队,进行着各自的“接寿”仪式。没有繁文缛节,他们只是肃立在祭坛前,闭上双眼,双臂微微张开,如同拥抱这天地间的风。
每一个人,神情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坦然。我们在连接,连接那看不见的长寿之缘。我学大家的样子,站上祭坛。当双眼闭拢,黑暗降临,感官骤然敏锐——
风穿过耳廓,拂过发梢,拍打衣襟的感觉被无限放大。我清晰地感觉到,那无数银亮的“风纹”丝线,正从虚空中探出,轻柔地、牢固地系在我的四肢百骸。

一种难以言喻的踏实与通畅感贯透全身,仿佛体内原来那些被生命年轮所淤塞的通道,都被这股天地之气冲刷、打通。心不由自主地变得无限虔诚,心中默默祷念:“让病痛滚远,让这身体,从此只合着山海的节奏运转。“这句话不是临时起意,而是刻在半山上一块怪石上的古训。
下得山来,重返人间,第一个遇见的,是邻近集市上一倍110多岁的婆婆。
她正背着一小捆新砍的柴禾,脚步轻捷地走在回家的青石路上。脸上沟壑纵横,是岁月的版图,但皮肤底下透出的,是健康的、饱满的红光。她与相识的乡邻打着招呼,声音清亮,口齿清晰。同行的本地人低声道:“阿婆今年一百零一十三了,还自己种菜、砍柴,每旬下山赶集两回,走这山路,比许多后生还快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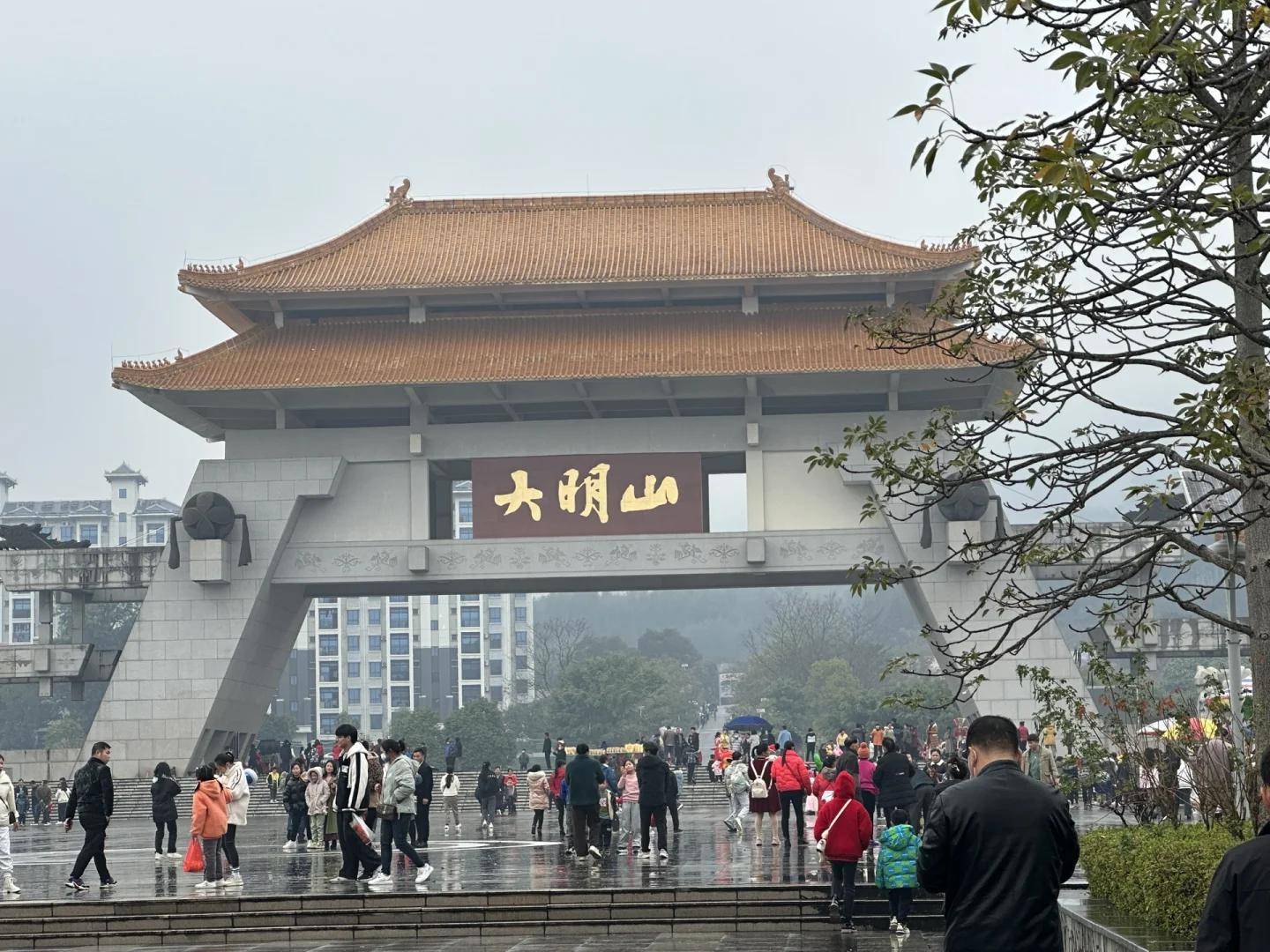
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,忽然完全理解了骆越王的话。长寿不是僵硬的年岁累加,而是一种与天地共鸣的生命姿态。他们吃得清贫,过得简朴,却因此卸下了物欲的负累,让身体这座桥梁,能最通畅地连接那永恒的生命之源。他们的灵巧,是风纹未曾僵滞的证明;他们的红光,是寿缘丰沛外显的华彩。
此刻,我虽已离开,手腕上那缕风纹的触感却依稀犹在。它提醒我,大明山永远在那里,风永不停止地歌唱,云幕上的寿星永远会准时出现。他等待着每一个愿意暂时脱离凡尘、前来“接寿”的灵魂。当你觉得尘世的身体即将朽坏,当病痛开始窥伺,不妨回到这里。

让山风洗去你体内的淤浊,让云海开阔你逼仄的胸襟,让骆越王指点那风纹的奥秘。然后,带着被延长的节奏、被刷新的身体,返回人间,去实现那百岁的最低目标,去仰望一百二十、一百三十,甚至更远的长寿殿堂。
这绝不是非痴妄。只要你记得,时常回来膜拜,回来连接。这人间至美的仙境,这长生奥秘的源头,永远为你,风鸣不止。